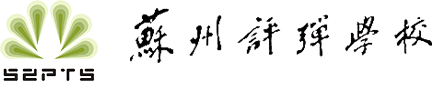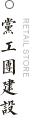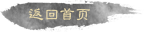苏州日报报道:把评弹唱进首届春晚——评弹演唱艺术家邢晏芝访谈
来源:苏州评弹学校 发布时间:2009-04-26 10:09:21 浏览量:3474
返回列表像我们这一辈艺人,如果不努力,就啃啃老本,我们还是过得去的,但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前辈呢?又怎么对得起后辈呢?———邢晏芝
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,应该从“根”上做起
会客厅:邢老师好!你是苏州评弹的传承人,而苏州评弹已列为“非遗”;既然是先人留下的遗产,那就势必有个继承和保护的问题,否则做后人的就是不肖子孙了。你这传承人,评弹学校的“掌门人”,请谈谈该怎样传承和保护的问题吧。
邢晏芝:谢谢。这个“保护”,从我的理解来讲,一个是博物馆的保护,就是将一些过去的东西原汁原味的放在博物馆保存起来。这些“旧东西”,也许一时是看不到使用价值的,但它的文物价值是非常高的,我们过去评弹界的老艺人的作品,声腔,可能没有现在艺人的这么完整,好听,但它们的价值,是“根基”性的东西,是千万不能忘记的。历史是不容否定的。过去“老先生”们留下来的本子啊,声腔啊,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,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保留下来,已经是很难得了。对待前人的成果,我们要像对待文物一样加以保护。这些作品,在当今人们浮躁的心态下,也许是很少人要听了,一些无知的人,还认为是很陈旧很烂的东西,但你将它作为一种文化,一个艺术门类来研究,不让它消亡,你是一定要用这些貌似“很陈旧很烂”的东西的。一旦没有了,才发现它的价值,但到那时就一切都晚了。
会客厅:邢老师对遗产的传承心情是急切的,也是胸有成竹的。你们这一代艺术家,是承前启后的中坚,相比别的艺术门类,评弹还是很幸运的。保护起来有现成的,不是处在“抢救”的境地。
邢晏芝:像我们这一代艺人,还是幸运地接触了一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艺人的,也真正地向他们讨教过一些东西。这是“根”,是“底气”。非物质遗产的保护,就应该从“根”上做起。然后,我们才可能摆脱一些浮躁的东西。
像我们这一辈艺人,如果不努力,就啃啃老本,我们还是过得去的,但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前辈呢?又怎么对得起后辈呢?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,还有五十年代,六十年代的初期,这一个时期,是评弹最兴旺的时候,人才辈出也在这个时候,流派纷呈也在这个时候,什么原因?充满着竞争力。当时的市场非常活跃,这是我们父辈们的市场。这个时候,出现了二十多种流派,给我们留下了一批跟上时代发展、跟上当时观众需要的一批宝贵财产,如今评弹走到二十一世纪了,我们评弹艺人更要认识这批财产的宝贵价值,要研究其中成功的原因。这里,继承是第一位的。我认为继承可以分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,叫“鹦鹉学舌式”,这也是保护的一种有效方式。“非遗”的传承,就是要由人来“传”的,要学,好好地学,才能留和传。第二阶段,我叫它“答卷式”,就是我们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原汁原味的东西,变成自己编排的东西,然后,送给老师验证、打分,送给观众验证、打分,这就是“答卷式”的学习。第三个阶段,就是找到了一个载体来发展自己。曲艺艺人,都是根据自己各自的特点来发展的。譬如一个嗓音条件非常棒的老师,独创了自己的流派,这可以理解;但一个嗓音条件不是很棒的老师,也照样能创造一个独立的流派,这是为什么?这是因为曲艺演员从来都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去吸取别人的东西,博采众长,找到了载体。载体有两个,一个是流派的基础,另一个是书目的基础。譬如我自己,除了名师的载体,我还有另一个很大的载体的空间,就是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的这部书。过去,书与演员,书与流派,是有机联系的。观众认你的人,再才是你的书。如人们说到严雪亭——《杨乃武》;蒋月泉——《玉蜻蜓》;先是人,后是书,人与书是紧密结合的。要真正创立一个流派,不仅仅是一首开篇一首词就可以的。要青史留名,公众承认,能够成为遗产流传下去,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从两个载体上发展你的流派。也只有这样,才可能谈到创新。
我们是代表众多的苏州评弹艺人走上春晚舞台
会客厅:邢老师,我们都知道评弹不及昆曲的历史悠久,但也是出了很多大家的,是苏州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。你能介绍一下评弹的历史吗?
邢晏芝:评弹艺术历史悠久,有说是起源于西汉,有讲从明末清初开始,单以说书来说,那是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朝代了,但用苏州方言说书而且夹有弹唱,我们一般认为,是清朝的王周士为起始人,流传到现在两百多年。最近评弹艺术被国家定为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之一。据统计,中国历史上约有五百多种文化遗产,现在留存约还有两百多种,消亡很快。评弹在陈云同志关心下,早在四十六年前就建立了专业学校,当时是国家认可的中专层次,学校运用了一些有利条件,吸引了一批青年来接受评弹教育,比较早从体制上解决了传承问题。是陈云同志超前的传承意识,评弹才有了今天。
评弹艺术的流派唱腔是前辈艺人流传下来的,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。现在的许多优秀经典作品就是经过一代一代艺人不断改革,不断发展,不断创造所取得的。从马如飞到朱雪琴,从魏珏卿到薛小飞,从俞秀山到朱介生,从周玉泉到蒋月泉,那是数代人共同努力创造的成果。我们的前辈在创造艺术辉煌年代互相合作,互相交流,互相借鉴,不乏动人的先例,给我们树立了榜样,也能不断地激励我们。
会客厅:苏州评弹,是苏州文化的名片之一,你与你哥哥邢晏春老师的兄妹档,多次代表苏州进京献演,最难忘的是哪一次,还记得吗?
邢晏芝:当然记得。要说我们进京演出,的确次数很多了,其中许多都是高规格的。第一次,应该是中央电视台的首次春节联欢会,我们兄妹档的评弹节目,有十多分钟,主持人是电影演员达式常。
会客厅:春节联欢会是全国人民的“大年饺子”,国内外的许多观众就是通过这里认识苏州评弹的,所以,你们兄妹对苏州文化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,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邢晏芝:那不敢当的。只能说我们的运气不错。可以说,我们是代表众多的苏州评弹艺人走上春晚那么隆重的舞台的。回首自己的学艺路,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家父邢瑞庭。他是很优秀的评弹演员,他嗓音条件好,肯学习,有天赋,所以学什么像什么,擅唱各种流派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,他一天要唱十几个电台,还开创了一档节目,专门介绍各种流派,有“开篇大王”的美誉。
会客厅:父亲是你们兄妹的启蒙老师?
邢晏芝:是的。父亲非常开明,从无门户之见,也不重男轻女,对子女的教导都是如此。他不但鼓励我学,还给我定下“三个非”:一是“非学不可”,二是“非会不可”,三是“非好不可”。后来我体会深刻,还为自己加了一句——“非创造不可”。
评弹是曲艺,无作曲,无导演,无乐队,评弹演员面对新的唱词都要自己来设计唱腔,因此学习时对各种流派都要有研究,研究式的学就是一种开动脑筋深入的学,既要研究老师的作品,还要研究自己碰到的问题,用老师的唱腔去设计老师没有唱过的内容。这是验证你学习的灵活程度。记得有一个研讨会,蒋月泉老师说:“现在有些青年演员不知道怎么的,拿到新的唱段自己不会弄,拿到我这里,要我先唱,再用录音机录下来,回去依样画葫芦学,这样很危险。”接着他自问一句:“不知道是啥道理?!”我当时在旁答道:“这是不动脑筋。”蒋老师听后大加赞同地说:“对!对!”
在老师的启发之下,我学了之后及时应用,用老师的唱腔来设计新的内容,而且还让老师来审核我的设计合理与否。这也就是俗话说的“师傅领进门,修行在各人。”
没有恩师的悉心指教,就没有我的今天
会客厅:能感觉出来,你是个很懂感恩的人,师恩在你的心中扎下了深深的根。
邢晏芝:没有恩师的悉心指教,就没有我邢晏芝的今天,我怎么能不感激他们呢?
除了家父的教导,与兄长的共同切磋,我还有幸在从艺道路上遇到几位良师,得到他们的亲口传授。比如祁莲芳老师,我们在上海闸北工人文化宫演出《十五贯》,我演的角色苏戍娟,是用祁调设计的唱腔。我是从父亲那里学的祁调唱法,当时连祁老师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有一天,祁老师来听书,手里拿着一只老式十三品琵琶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,一位忠厚长者。他对我说“晏芝啊,我在人民公园喝茶,有人告诉我,说有人在唱我的祁调,不怕后继无人哉。所以我特地赶来听一听。”祁老师非常乐意教我,于是我就正式拜他为师,我们到闵行演出,祁老师又跟到闵行。相处了三天,祁老师把自己所有的唱腔都让我录下来回苏州加深学习。后来,我和他老人家通信往来,我对他的称呼是“敬爱的老师”,他对我的称呼很有趣——“敬爱的爱门生”。
还有不能不提的王月香老师。王老师是我评校的同事,她的唱法我以前不敢学,总觉得跟我的路子不同。有一次,我们一同在校值班,她叹息说,自己一曲《英台哭灵》太长,无人愿意给她记谱。我主动承担这一工作,于是她认真唱给我听。王老师的认真是出名的,教学生的时候一曲唱罢自己也会泪流满面。我不但把谱记下来,还把她的用嗓方法、用气方法也解读了。她演唱时吸气方法与众不同,一般人在强拍上换气,她却在弱拍上换,对情绪宣泄有独到的技巧。之外我还要王老师把对人物的理解、内心独白都跟我讲一讲,我感觉自己学的不仅仅是王老师的形,更还有她的神。
特别要说的是杨振雄老师,我也是他的入室弟子。他生前不厌其烦地把《挑帘》、《太白醉吟》、《絮阁争宠》中各个人物的喜、怒、哀、乐的情绪表演,以及杨派艺术的唱腔,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。在杨老师身上,我学到了超凡脱俗的表演艺术。后来在演绎《四大美人·贵妃篇》中《马嵬坡》里杨贵妃的一段唱词时,我非常用心地用杨派俞调设计唱腔,受到内行专家和听众们的一致好评,这也是我给杨老师的一份答卷。不知杨老师在天之灵是否满意。
会客厅:重情重义的好学生。我听着都不由感动了。感觉你的艺术实践,就是要做集大成者,敬重前人的成果,同时,还要结合自己的天分,走出自己的路,创自己的流派。所以说继承与创新是紧密相关的,继承得越好,也就越能创新。
邢晏芝:是这样的。评弹是这样,别的艺术门类也无不是这样。
评弹音乐并不复杂,只有一个主旋律,一曲多唱。但各种流派用嗓方法不同,发音位置不同,运腔内涵不同,韵味也不同,加上节奏、情感处理不同,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风格。
我在大量学习前辈的同时,也对自己进行了研究,觉得音域宽的唱法比较适合自己,纸大才好作画,在运腔上能有很大的空间,尽情地抒发。
这里,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哥哥邢晏春,本来《密室相会》,原本是男角的戏,女角色很容易成“插蜡烛”,“摆花瓶”,但是我哥哥文字好,非常能写,他将女角的戏充分激活了,才有我们共同的成功。
邢晏芝小传:
国家一级演员苏州评弹学校副校长,国家文华表演奖、牡丹奖获得者,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,江苏省劳动模范,江苏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,江苏文体十佳。主要代表作品:长篇弹词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、《贩马记》、《三个母亲》、《三笑》,以及“密室相会”、“杜十娘”、“林黛玉”、“贵妃篇”等中篇、选曲、开篇。参加数十次中央级重大演出活动,举办“莺啼燕语唱新声”个人演唱会。
(原载2009年4月26日《姑苏晚报》)